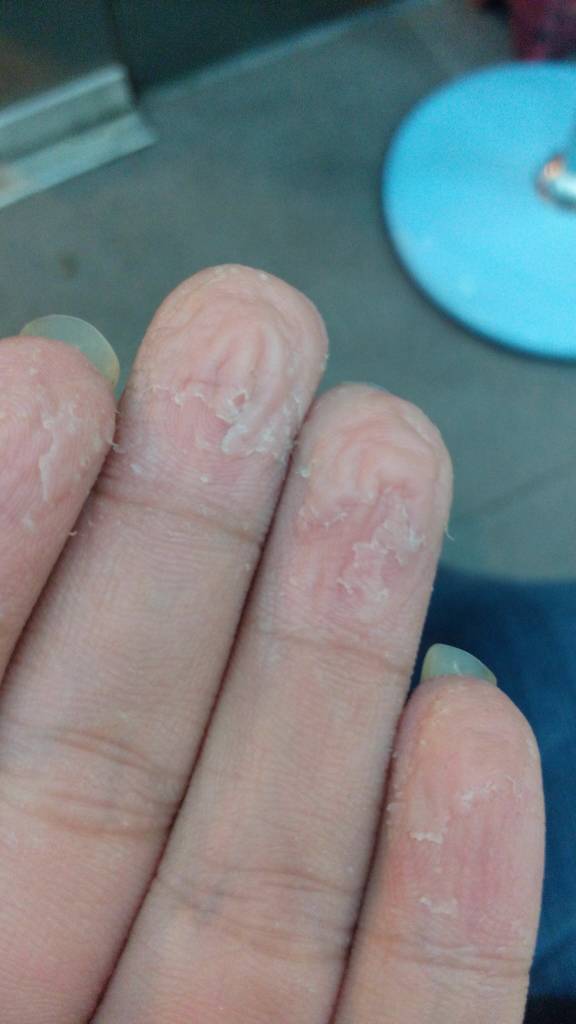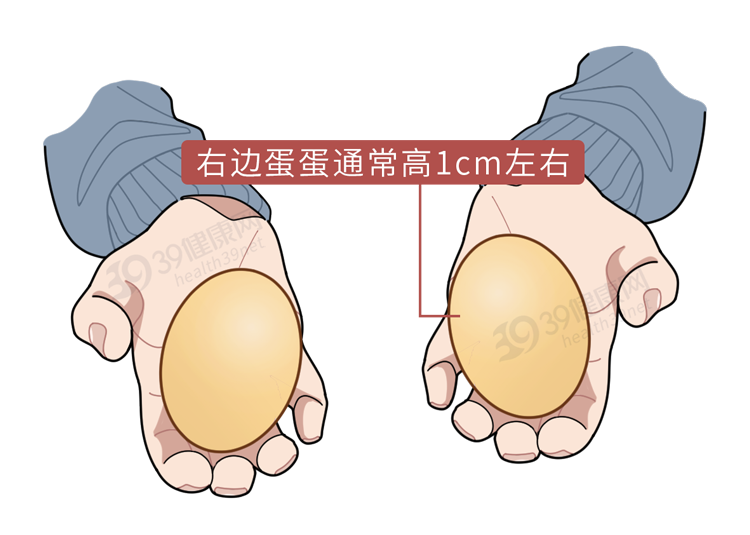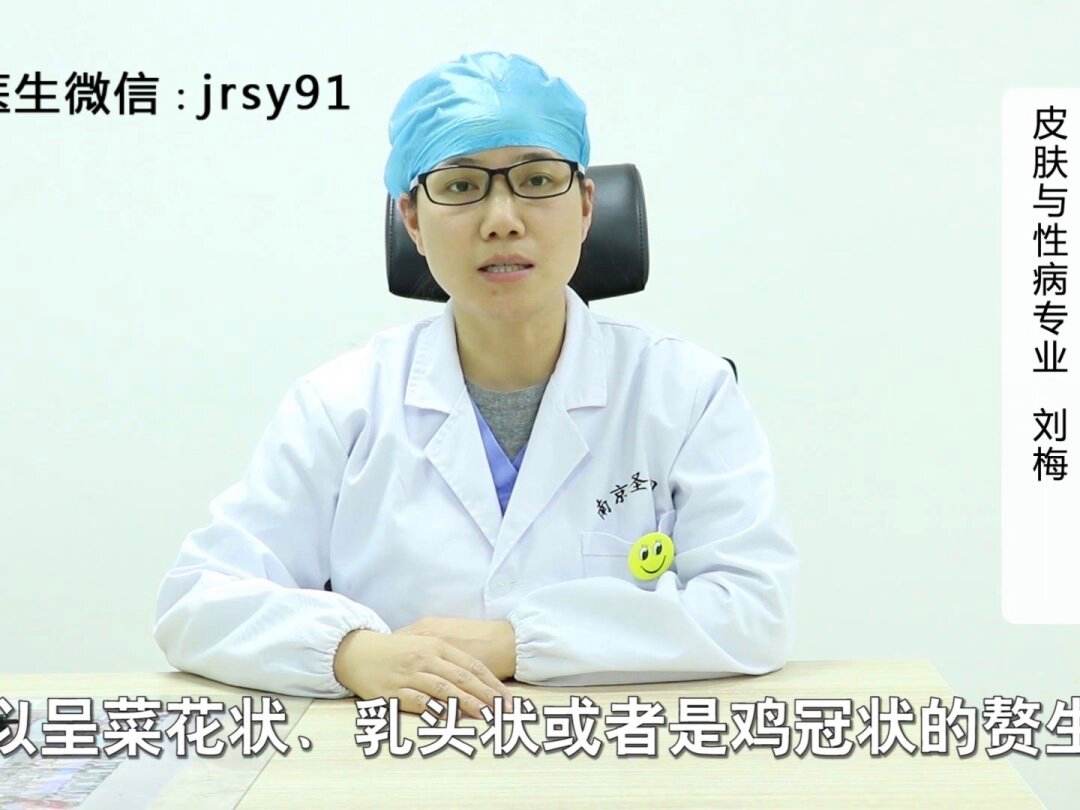门
骆礼俊
一根水泥柱子和贴有黄色瓷砖的墙壁之间,有两扇铁架子门。组成门的栏杆锈了,黑漆翻卷起来,像枯萎了的细小树叶。铁门的上边,为防人随意翻越,做成了梭标一样的铁尖,直指小区圆形的天空。这两扇铁架子门,看看小区里还发亮的墙壁瓷砖,就知道它的年龄还不大,可它却实实在在地老了。它歪歪斜斜地像个精神病人似的站着,连接水泥柱和墙壁的合页都裂了缝了,一阵风,或许也能把它吹倒。但它却不倒,一些小孩在门上荡秋千,它叽叽呀呀的,还在给孩子门鼓着劲。
这个小区里,有八十来户人家,啥样儿人都有。有当官的,做生意的,教书的,从农村搬进城的……老张六十多了,一辈子都在乡村中学任教。儿子在外打工挣了钱,就买了这小区里的一套房子。老张和老伴进城后,儿子媳妇又外出打工了,只把孙女交给老两口带。老张每天的工作就是接送孙女上学,没事了闲得慌的时候就到小区外面的一家茶馆里喝喝茶,打打牌。说是茶馆,实际上只不过挂个名,重点业务是招赌,抽取赌资。老张和一帮老头老太打麻将,赌资很少,权当混时间。老板娘也没意见,人气才是重要的。在一个小房间里,总有许多年轻人赌金花。红红的百元钞票在桌子上像纸一样被年轻人们扔来扔去的。老张不打麻将的时候就在一边看,看得双眼都鼓成鸟蛋了。他看到一位小青年,别人看牌他不看,一个劲儿地往桌上扔钱,这种赌法叫扪。扪的钱越多,看了牌的人就得多拿出一倍的钱。那小青年都扪了好几百了,还不看牌,最后就扪起来三张清牌,钱也赢了一大堆。老张倒不羡慕,十个赌鬼九个输,为赌倾家荡产的例子多得很。有位财政所的工作人员,不是就因为赌而进了监狱了吗?嗨,好好的工作,丢了,多不合算啊。
老张看看孙女放学的时间到了,就不打麻将了,来到学校门口,伸长脖子往鸭群似的人堆里瞅。有时他还没看到孙女呢,孙女就抱住了他的腿。老张不担心孙女走丢,有次没接到,孙女也自个儿能回去。老张担心的是过小区的铁门。那铁门摇摇晃晃的,倒下来连壮小伙也能砸扁,何况抱不住老母鸡的孙女儿呢。老张也不知叮嘱过孙女多少遍了,要她不要爬在铁门上玩。出铁门的时候要快,不能摸铁门。见有别的小孩在铁门上玩,就不要过去。孙女儿都能背诵老张的话了。孙女儿都有些烦了。可老张就是悬着一颗心,无论刮风下雨他都要去接送孙女。那次在学校没接到孙女,老张就感觉天都要蹋下来了,心砰砰跳着,急急的往回赶时脚下都打起飘来了。有牌友和他打招呼,他也没停下来,一不小心就踩虚了脚,摔了个狗吃屎,还好没有大碍。一直到看到孙女儿鲜鲜活活的在家里蹦跳时,老张才瘫坐在沙发上,好像生了一场大病似的。
老张牵着孙女柔软无骨的小手,又来到铁门前。一个扎着羊角辫的小女孩和一位戴着空军帽的小男孩正在铁门上玩。他们大约也是看过美国电影《泰坦尼克号》的,学着男女主人公在船头的动作。小女孩站在下边横着的铁栏杆上,小男孩则站在上一根铁栏杆上,俩人背贴铁架子门,双手分开,反手抓住铁架子门,做成一个凌空飞翔的动作。不知是哪家的音乐正舒缓奏响。小男孩的头随着音乐的节拍一点一点的,每点一下,老张的嘴就张一下,缺了门牙的嘴就哈进一口风。老张每咳一下,就退后一步。老张终于不咳了,大声的吼起来:“下来,下来,你两个小东西下来,危险。”两个小东西根本没把老张放在眼里,他们为老张的着急样儿咯咯地笑了。孙女早就等得不耐烦了,她的肚子都咕咕叫了。孙女的小手在老张的手里挣扎。老张捏得更紧了。不能过去,饿了爷爷给你买蛋糕吃。孙女说,不吃不吃,就是不吃。老张见俩小东西还在铁门上荡来荡去,怒了,出言就不吉利了。老张说,铁门倒下来会砸死你们的,你们的大人死到哪儿去了!老张的话刚完,一双高跟鞋的嘀嘀声就响到了他面前。说的哪样话?铁门砸人也睁眼呢,专砸良心坏的人。老张就瞅向高跟鞋的主人。这是一位衣着时髦的年轻女人,婆浪形头发垂在脑后,一双秀眼里蓄着怒气,就连嘴上的那颗美人痣都跳起来了。年轻女人也意识到危险性,来不及进一步责怪老张就向铁门冲去,把小女孩抱了下来。小男孩也恼恨地盯了老张一眼,这才恋恋不舍地从铁门上跳了下来。迅捷地穿过铁门的时候,老张突然觉得自己和孙女是一老一少两只鱼,而铁门就是一张网。
老张的书桌上有一本影集,大多数是他和学生的留影。学生们的造型,大多很俏皮,或做着鬼脸,或吐着舌头,或手搭凉棚,或猴子探月……最有创意的,是一位名叫马海波的同学,他在眉心画了一只眼,做一个二郎神大战孙悟空的动作。老张凝视着马海波,笑不出来,面部表情开始扭屈了,眼里也潮湿起来。多好的学生啊,可他却夭折了,都是学校那该死的铁门啊。谁都没有注意那扇铁门是何等的阴险,它审视着每天进出的几百张笑脸,正准备吃掉其中的一张或者两张,甚至更多。马海波是劳动委员,和往常一样,同学们搞完卫生了他要重新检查一遍。他看到铁门拐角处有一张蜘蛛网,蜘蛛网粘住了一些灰尘,蜘蛛却不知躲到哪儿去了。马海波用一把扫帚去拂那蛛网,可够不着,跳起来再拂,仍然差着一大截。马海波就沿着铁门,攀爬了上去,费力的把扫帚伸向了蛛网。躲在墙角的蜘蛛还以为是猎物上钩了呢,正想过来猎取,却被扫帚拂疼了,慌忙间从屁股冒出丝来,快速垂向地面。也不知是不是蜘蛛的牵引力太大,那铁门倒了。铁门压在了马海波身上,而蜘蛛则被马海波压在了身下。那只被压住的蜘蛛是老张抱起马海波冲向医务室时发现的。蜘蛛依然能够爬行,可从马海波身体里流出的血让他的几只脚有了粘滞感,就像人在稀泥里行走一样。老张恼恨这只蜘蛛,放下马海波后,他掐住它扔出了老远。
老张看着马海波的照片,脑子里重新有了一只蜘蛛在爬,并且吐出了无数的丝,把他的整个脑袋都缠绕住了。蜘蛛犹如变色龙,瞬间就从黑色变成了红色,继而变成深红,透明了。肚里好像什么东西也没有,似乎全是可以转化成丝的物质。老伴在身后捅了他一下,老张才清醒过来,一滴泪终于落在了相片上。老伴一下夺过影集,责备道:“又不是你的错,这么多年了你咋老是放不下呢?我拿去烧了。”老张突然愤怒地大叫一声:“你敢!”老张的吼声让孙女“哇”的一声哭了起来。老伴只得把影集又还给了老张,抱起孙女,嘀咕着退出了书房。
老张到杂物室里翻来翻去,可大多是一些朽烂了的纸片或木棒,没有他要找的八号铁丝。老张问老伴:“铁丝哪去了?我记得有一圈的嘛。”老伴这时仍在气头上,当然没有好回答:“我是保管员啊?晓得我也不给你讲。”老张就“嘭”的一声关了杂物室的门,说:“你不讲我还没得办法呐。”老张带上铁钳,到五金店买了一圈铁丝,回到小区铁门前忙活起来。挨柱子的一面,只需要圈住就行了,而挨墙壁的一面,铁丝就没有可固定的地方了。老张反复地察看,可终久没有可靠的办法。望着那扇依然歪斜着像二流子一样的铁门,老张无计可施了。最后是去了电脑打印部,让打字员打了一行字:小心!铁门倒下会砸死人。老张读了两遍,觉得措词不太好,就又重新打印:别碰我,我倒下的同时你也有可能倒下。老张拿着打印的警示标语来到小区门前,贴在了铁门旁边。
老张还没离开,一对夫妇领着一个小男孩回来了。小男孩对老张贴的那幅标语很感兴趣,问爸爸什么意思。爸爸刚解释完,妈妈就强调说:“伟伟,如果见到有别的小孩在铁门上玩,一定要离远点。”这个叫伟伟的小男孩说他从未摇过铁门。伟伟又问爸爸,说这门都坏掉了,为什么没人来管?爸爸说这本来是开发商的事,现在开发商赚钱走了,又没有物业管理公司入住,所以就没人管了。
“那,爸爸,你为什么不管?”伟伟仰起脸问爸爸。
伟伟的爸爸不知该怎么回答,妈妈接过话头说:“你没看见爸爸忙吗?况且这是大家的事,得大家管!”
伟伟还想说点什么,妈妈却不由分说地拉着小男孩快速穿过铁门,回家去了。
一旁的老张陷入了沉思。
老张决定由自己出面向小区八十多住户收取资金,对铁门加以修缮和加固,及早消除隐患。
当天下午,老张就挨家挨户敲门收钱,前几户收得比较顺利,还对老张的这种奉献精神表示赞扬。可当老张收到第七户时,开门的正是早上放学见到的那位嘴上有美人痣的时髦女郎。那女郎问:“你是小区主任?”老张摇头。女郎没好气地把门“咣”的一声关上了,豪华的防盗门扇起一阵风,让老张不自禁打了一个颤。老张想再次按响门铃,但终于缩回了手。
老张换了一个单元,敲开门,开门的是个秃头男人。老张说明来意,秃头男人说想看看老张的身份证。老张说没带在身上。那男人很干脆,说那就等你把身份证拿来看后再给钱吧,说完不由分说也关了门。老张苦笑一下,接着收其他住户的钱,可一个住户比一个住户刁钻,一个住户比一个住户古怪。老张磨干了嘴皮,才收了两百来块钱,回到家里,浑身像散了架,老伴边给他捶背边骂他傻。
第二天,老张没有再挨家挨户收钱,而是把自家的报箱取下钉在了小区大铁门边上,还贴了一张倡议书:
为了你和家人的安全,请把你的零钱投进这个报箱里吧,我将用这笔钱把铁门加固得结结实实,雷打不动。另,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希望尊敬的小偷先生别光顾这个报箱,因为铁门一旦倒下,压着的也有可能就是您。
老张躲在自家窗户前注视着小区门口的那个报箱。孙女儿以为有啥稀奇好看哩,也把小脑袋挤过来,然而她只看到满地的阳光以及晒着阳光的塑料纸屑。小区里本来也有几个月牙形的花园,可花园里的花却蔫了身子,倒在杂草丛中了。有哪样好看嘛,孙女嘟着嘴走开了。老张依然一动不动地盯着报箱,双眼被反射来的阳光灼痛了,有些模糊了。进出铁门的人很多,老的少的男的女的,可他们见到报箱后都一笑置之,根本没有人向报箱里投进那怕一毛钱。人们进出铁门的时候,也是急匆匆的,不知是害怕铁门真的倒下还是有什么急事。
一个小男孩从楼梯口搬了张凳子出来。那凳子很大很沉,小男孩搬起来很艰难。他在阳光下放下凳子,擦了擦额上的汗水,然后再把凳子搬到了报箱前。老张不知道小男孩要干什么,就一眨不眨地盯着。小男孩并没有爬上凳子,而是飞快地转身回了楼梯口,没多久小男孩又出来了,手里却多了一个东西,好像是一只雪白的兔子。兔子反射的阳光在小区墙壁上形成了一个不规则的光斑。老张便明白那不是一只真正的兔子,而是一个存钱罐。老张突然兴奋起来。果然,小男孩是要把存钱罐里的硬币投到报箱里。小男孩投硬币时,有一枚没投进,滚到了水泥地上。那硬币在地上欢快地转了几个圈儿,不知藏到哪块果皮下面去了。小男孩就仔仔细细地找,可找来找去都没有找见。老张急急忙忙下了楼,见弯腰寻钱的小男孩就是那个叫伟伟的小男孩,不禁又想起了昨天伟伟和他爸爸妈妈的对话。一老一少把报箱前的垃圾翻遍了,终于把那枚想逃的硬币找着了。硬币“当”的一声被投进了报箱,小男孩笑了,老张也笑了。
老张怎么也没想到,他挂在铁门边的报箱竟然被人砸成了八块,里边的硬币也不冀而飞。砸报箱的人还挑衅地在倡议书边上写下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狗东西,气死我了!”
报箱被砸的事在小区传为笑谈,老张也气得病倒在床上。
几天后,老张恢复了身子骨,对老伴说:“今天我要去打麻将。”老伴说:“儿子挣钱不容易,你还是别糟蹋他们寄来的血汗钱吧。”老张没有听从老伴的劝阻,出了小区铁门,然后又回转身,盯住铁门。老张下意识地看看天,一片云彩也没有。
来到茶馆,一帮老牌友热情地招呼老张:“来来来,三缺一。”老张说:“今天我不和你们玩小牌,我要和年轻人赌金花。”
“算了吧,老张,凭你那技术!还是和我们玩吧,权当娱乐嘛。”有人劝说老张。
“不怕,即使输了,输的也是别人的钱。”老张气乎乎的说。
“谁的钱?”一位老头奇怪地问。
“别人凑的,两百多,不输白不输。”老张停顿片刻,又补充说,“不过我相信老天有眼。”
老张不再理会那些老牌友的追问,要来一壶茶,慢慢地喝。茶很香,一缕热气悠悠地像根曲线似的升起来。老张用手抚胸膛那儿,感觉一颗心砰砰地跳得厉害,身上也热乎乎的。茶馆的天花板上,一只蜘蛛正悠闲地坐在蛛网中央,目不转睛地盯着老张。老张感觉心里有些发毛。一壶茶很快见了底,可老张仍然觉得很渴。老张把茶叶也倒进嘴里,嚼起来。老板娘走过来想问老张今天是不是身体有些儿不舒服,可老张却起身朝赌金花的小包房走去。
包房里烟雾弥漫,空气相当污浊,地上的烟头都快铺了一层了。赌金花正赌到了高潮,十几双眼睛,都瞪圆了。钱,在桌子上堆成小山了。一局刚完,老张坐在了一张椅子上,说:“给我也发三张牌。”老张的声音很低,可小青年们都听到了,目光唰地集中到老张身上。老张身子缩了一下,然而他依然坚决地说:“给我也发三张牌。”一位年轻人把牌洗得哗哗响,果真就给老张发起牌来。老张从未赌过金花,但他早就看熟了,懂得游戏规则了。老张把牌小心地翻开一道缝,一副臭牌,一圈也没走就不要了。如是接连几次,老张连一个A也没有得到。一位年轻人就拍了老张的肩膀一下,说老人家你看仔细哈,别把清牌也当成杂花牌扔了。老张没好气地说,我眼还没瞎呢,老天爷却瞎了。十来局过后,老张从小区住户收来的两百多块钱就输光了。老张心里默念着,最后一局,最后一局,再输就走,一辈子不赌了。翻牌的时候,老张觉得三张纸牌就像三块石板,沉得很,但终于让老张看清了,三个A,天哪,最大的牌了。老张的心砰砰跳了起来,手抖了起来。有人碰了碰老张,问他到底要不要。老张醒过神来,连声说,要,要,全要!
老张最终没赢到钱,用老板娘的话说,心里素质不够好,拿到大牌别人一眼就看出来了,谁都不是傻子啊。
出了茶馆,老张被一地的阳光刺得睁不开眼。小区那扇歪歪斜斜的铁门,挑衅地望着败兴而归的老张,似乎在说,你个老家伙不是想赢点钱来整治我吗?输了吧,老家伙!老张怔怔地盯着铁门,狠劲上来了。他回转身,向铁匠铺走去。一路上,老张都在咬牙切齿地念叨,输了咋啦?输了咋啦?老子用一个月的工资还治不了你,狗日的铁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