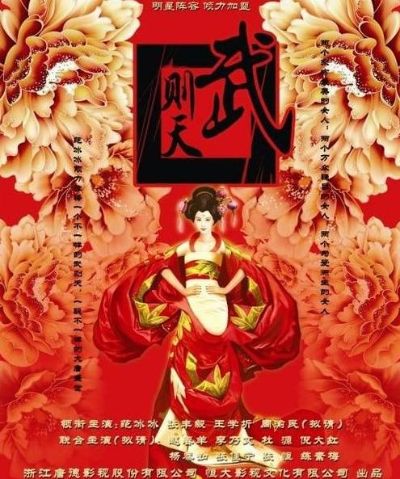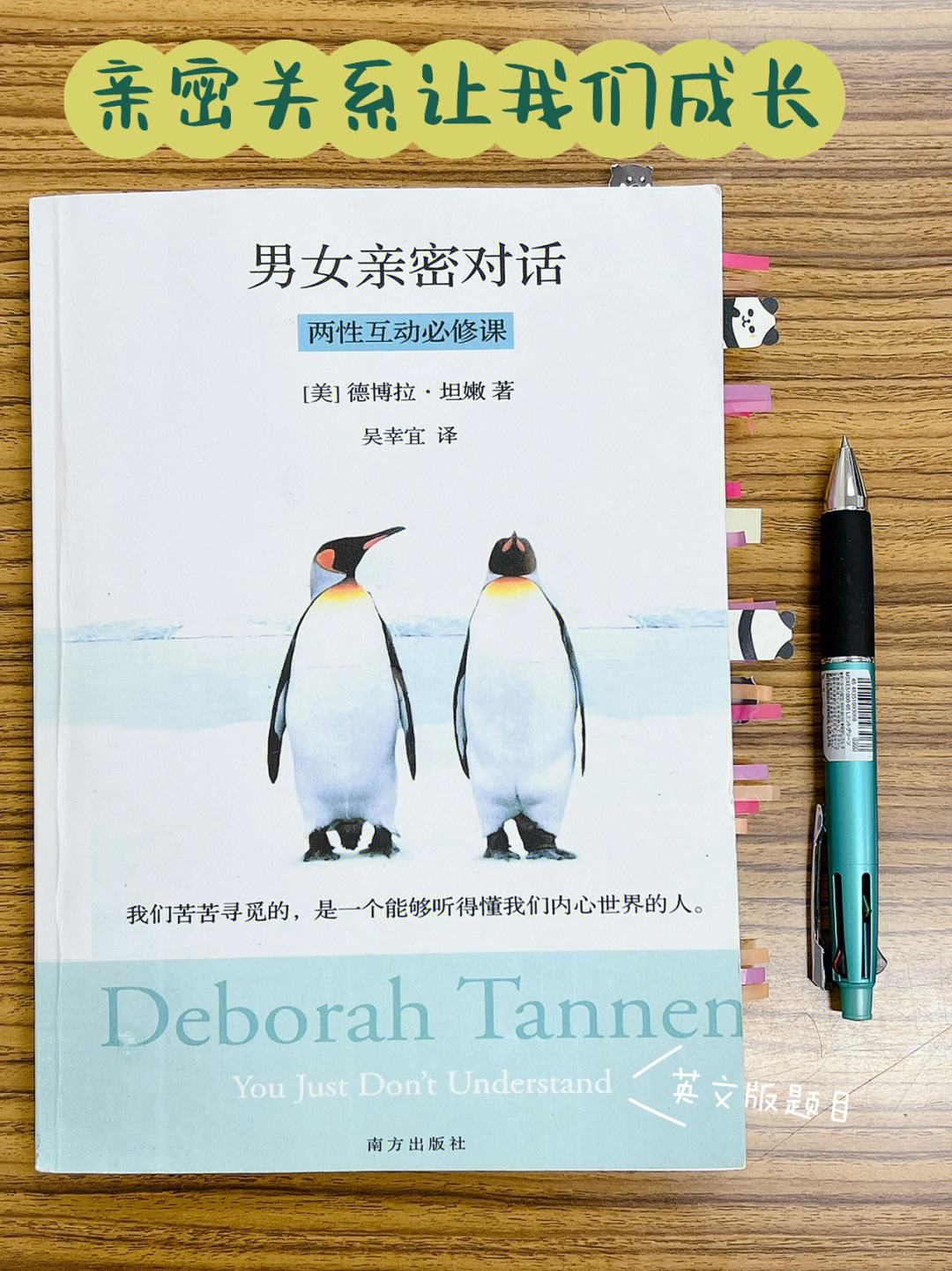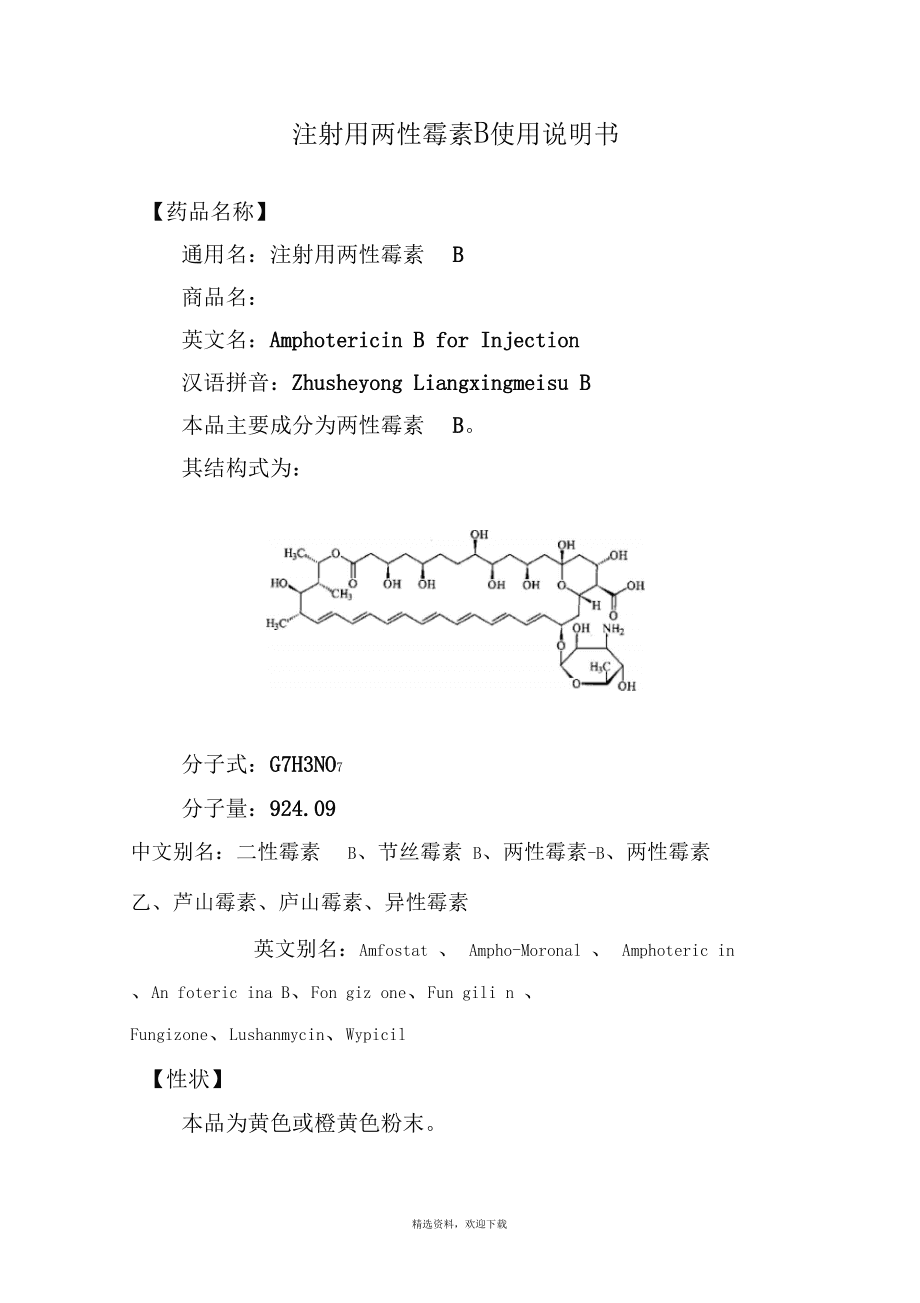九丹,江苏扬州人,原名朱子屏,1968年出生于江苏,1990年从中国新闻学院毕业,分配到广西一家报社做记者,后辞职到北京,还成立了一家企业,承包北京电影学院电视片部。
1995年留学新加坡,在异域学习和生活5年之后,于2000年回国,在北京一家周刊社做记者,业余时间从事创作。她是早年最具争议话题的女作家,用她“文坛罂粟”的独特笔触,创作出了被广泛讨论的《乌鸦》、《漂泊女人》等身体文学。
《乌鸦》我是很早前就断断续续的翻过了的,觉得这个女人太张扬和没头脑,胸大无脑,是可以原谅的。2002年,一位挚友专程从武汉书店给我带了《女人床》这本书,依稀记得当时一直搁书架上,偶尔翻翻,直到第二次翻起时,才一口气把它读完。回翻封面,上书“九丹洗尽铅华打造《女人床》。《女人床》之后,九丹将隐姓埋名远走他乡”。
洗尽铅华,似乎是这样的。小说以刺刺的笔触描写了两个底层女子从相识到相依、相爱和最终悲苦无奈的另类爱情故事。有人说这是一部非道德小说,但这实质上也更加印证了九丹作品的独特魅力:九丹何以是九丹?因为她总能把目光直戳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并且把阴暗部位端诸于阳光之下。不管是道德还是非道德,读她的作品,反而有些觉得就是在读现世的我们。九丹强调她的作品浸透了“忏悔”,但这并不足以平息人们的愤怒。最为气愤的是当时那些在新加坡的中国人,咒骂《乌鸦》的人说,《乌鸦》哗众取宠地将部分阴暗角落的东西,描绘成整个社会,“一竿子打翻了一船人”,丑化了中国女性的形象…… “如果说,在《乌鸦》里,她(九丹)把女人的衣服脱光了,那么在这部《女人床》中,她又把男人的衣服脱光了。”阿伯——《女人床》的男主人翁在这本书的后记中写道。
我是女人,见不得九丹脱女人衣服,但却并不介意她去扒男人的皮,甚至还乐于观赏。海明威与妓女麦子喜欢像海明威那样的老人。她跟穷人阿伯在一起的时候称自己是“知识女性”,她跟阿伯之外的两个有钱男人在一起的时候她称自己是“妓女”。“为什么女人们才刚刚开始,男人们就已经结束了?”这是麦子对感情关系的体会和理解。阿伯却认为她说的是性高潮。
麦子在认识阿伯之前在北大读MBA。委屈而压抑的边缘化阿伯在回忆自己的大学生活时,总结的句子是“委屈而压抑的青春”,就这样引起了我的共鸣。他是一个自诩为有才华的知识青年,过着自认为“边缘化”的生活。认识麦子之前他去发廊找便宜的妓女,认识麦子后他以为自己可以不用去找妓女了,可是他只是这么以为。阿伯是一位硕士研究生,写过一本名为《长安街》的书,整个小说里他干的所有正事就是为将《长安街》拍成电影而到处扎钱。

零距离的协调
阿伯有个观点:“男人的射精和女人的流产一样,是老天为了平衡性爱给人类带来的快乐所做的一次协调。”相应的麦子有个零距离理论:“你们男人没有情人,也会花钱去找妓女,但当一个女人天天跟你们在一起,你们又会说做爱伤身体了。”于是阿伯感叹:“你的确跟一般的妓女不一样,因为你能把自己体会的东西以规范的句子表达出来。”——看到这里时,我忍不住想骂:“可恶的男人!”
九丹的《女人床》,看得压抑却舒畅。
这本书已然是赤裸裸的在讲述着这个时代男女的情和事。故事发生在身边的地点,“西四的发廊”“东四的妇产医院”“宣武门的SOGO”“凯宾斯基饭店”。人物,二十七岁的女人,同样是青春的,知识的,物质的,有欲望的;不得志的男人,他们的懦弱与妥协,我们随时可以感受得到;成功的男人,他们的嚣张与卑鄙,我们可以不费力气的体会到。观点,男、女,欢、爱,知、性,钱、权。小说中以分角色叙述的手法来展开情节,用阿伯和麦子两个人物交错表述的方式,不断的变换人称,没有阅读阻碍却觉得读起来更顺畅,心理变化和矛盾的升级都因此显得很自然,事件的叙述角度也更显充分,人物更加丰满。
麦子其实是一个处在这个时代中低层的女子,可是遇到白泽后她开始摆脱不了物质生活的诱惑,她的欲望膨胀到自己无法满足而只能靠男人来填满的程度。白泽使她感情受挫和她遇到阿伯几乎是同时发生,她自然而然的爱上了这个落魄才子,同普通女孩一样爱的执著真切。阿伯第一次见到麦子就觉得麦子皮肤彷佛女神的皮肤一般。这个每次被麦子感动都会落泪的男人,却承受不了麦子对他的爱的回报。
当他们零距离时,他的心开始开小差,厌倦来的轻而易举。这是已经深陷的麦子措手不及的。麦子不是普通女孩,因为她总能勾起男人征服她的欲望。这在她遇到陈左时得到证实。她理所应当的接受了陈左给她的物质诱惑,并且幻想仍能将心留在阿伯那里,于是她在两个男人之间跳来跳去。在陈左要求麦子陪她去深圳出差的时候,她面临一个抉择,只是最终她还是选择了阿伯。这个举动让她显得异常可爱和美好,也映衬出之后阿伯那笔交易的无情和卑劣。陈左那样高傲的男人是无法接受麦子在他与阿伯之间如此踟躇的。于是他决定阿伯做交易,却没想到阿伯竟然会跟他讨价还价,最后他以两倍于他期望值的价钱买下了麦子的归属权。可是他高估了自己的实力,在被沈灿掌控的生活中,他没有那么多自由可以给另外一个女孩归属的。
初见沈灿时,麦子是骄傲的,她的资本是她的青春。可是在和沈灿被类似恐吓的谈话后,她才发现了一个拥有无限权利的女人是多么的可怕。可是她竟然瞬间产生了“想做沈灿那样的女人”的想法,并且在成为陈左的情人后希冀这个男人可以把她培养成沈灿那样的女人。这是一个妥协的想法,一个卑弱的想法,和沈灿是一样对权利极度渴求的麦子,却天真的以为这一切可以通过男人实现。
麦子更多时候让我觉得是纯洁和天真的。她跟白泽在一起除了房租和学费,生活是靠自己作记者兼职赚来到;她在阿伯总拿她和妓女来说事的时候,也能爱着他甚至不惜放弃自尊;她看着陈左在做爱前戴上安全套,竟然浑身冒冷汗认为那是对她的污蔑。这些,让麦子显得很可爱,很可怜,很可悲。九丹在小说里似乎刻意的将女性作了美化,麦子是一个梦想太多的女人,会有人同情和悲悯她;沈灿是一个能控制所有男人的女人,会有人仰视和敬羡她。相反,里面几乎所有男人都显得那么的丑恶。
不管是阿伯的软弱和妥协,还是陈左的无能和病态,还有白泽的道貌岸然,导演的懦弱猥琐,甚至还有麦子爸爸的老一代政客所特有的虚伪。就这样,我从书中目睹了九丹把男人的衣服扒的精光。阿伯在后记中还说,九丹,她看上去像一个朝气蓬勃的寡妇。
这个朝气蓬勃的寡妇问道:“床是欢场,还是归宿?”
“女人,在床上凌迟着赤裸的灵魂!”